核心提示:而打过人者,或打人致残致死者(据《北京日报》1980年12月20日报道,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,红卫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),虽然也经受着心灵的煎熬,但若是真的站出来道歉,或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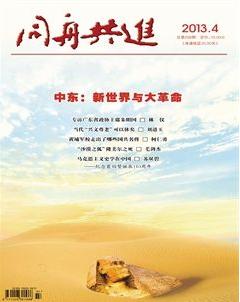
本文摘自:《同舟共进》2013年第4期,作者:赵勇,原题为:红卫兵的打人与道歉
读邢小群老师的《我们曾历经沧桑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),里面有访谈贺延光的部分。邢老师问:“文革”初批斗老师是不是你领头?贺延光答,他没有领头参与批斗过老师,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,年纪小,很自卑,对自己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。“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,我是一个观望者,既没参与,也不知道制止。为什么不制止?因为那是‘革命行动’”。而他分析自己没参与打人,深层原因与父亲的教育有关:“我父亲在社会上刚乱的时候就警告过我,说:解放军的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,有一条是不虐待俘虏。现在社会这么乱,有的红卫兵打人,甚至打死人,这是违反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的。我父亲对我讲别的道理,可能没有用,但讲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,是起作用的。因为我从小就把当兵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,而‘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’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。所以打人的事我从没参与过,这真的应该感谢我父亲。”
我对这段文字感兴趣,是因为学期末时,清华大学的一位学生辗转与我联系,说要写关于红卫兵的期末论文,有两个问题想对我做一访谈:一、为什么红卫兵打人?二、为什么打人之后不道歉?本来我是没有回答问题的资格的,因为我既没当过红卫兵,也没对红卫兵现象作过专门研究,但我还是回了封长邮件,陈述了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。
关于第一个问题,我的答复大体如下:打人在“文革”期间可能首先意味着“政治正确”,具有某种合法性,所以红卫兵小将们面对他们的批斗对象,往往会诉诸武力。而这种局面的形成,很可能与长期的仇恨教育、斗争哲学有关。众所周知,以前奉行的是斗争哲学,是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,其乐无穷。而既然要斗,就要斗出一个结果,就会不择手段。这种哲学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到教育机制当中,成为一些课文的内容(如斗地主、打土豪、分田地等),从而让“阶级仇,民族恨”在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。所以以我的推测,红卫兵打人并不那么简单,这种行为应该是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的肢体化反应。
另一方面,暴力美学借助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,也对青少年构成了一种长期的熏陶,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占领了他们的无意识领域。钱理群曾写过《1948:天地玄黄》(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)一书,其中分析过《太阳照在桑乾河上》和《暴风骤雨》中斗争的场面,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:“群众性的暴力,被描写成革命的狂欢节,既是阶级斗争的极致,也是美的极致:作者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强暴的美……”这种强暴的美既然已成新的美学原则,也就意味着暴力经过美学的包装不但具有了合法性,而且具有了某种示范性和观赏性。与此同时,暴力美学又借助于文学作品、电影、连环画等媒介,开始向日常生活渗透,以致成了人们追求模仿的样板。
除此之外,我还谈到了青春叛逆期的心理特点。当一个社会比较正常时,那种与父母较劲、向社会叫板的逆反心理还会约束在理性的河床里,而不至于酿成灾难。但当全社会都非理性起来之后,借助于这种社会氛围,逆反心理不但会变成一种心理宣泄,而且还会得到某种保护。于是,在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的武装下,打人便成了堂而皇之的事情。
这位学生想让我挖掘一下打人的深层原因,我想我也就只能挖掘到这种程度了。而与第一个问题相比,第二个问题却不太好回答。我首先想到的是,打人之后道歉,其前提是他们能认识到此种举动极端错误,如果不承认这是错误之举,道歉也就无从谈起。我之所以想到这一层,是因为张承志曾用日文写作并出版过一部《红卫兵时代》。关于这本书,他曾写下如下文字:“我毕竟为红卫兵——说到底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词汇,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和叛逆性质,坚决地实行了赞颂。”(《无援的思想》,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)这意味着张承志在反思红卫兵现象时主要是在肯定。这当然不是说他也在肯定“打人”正确,但问题是,如果一些人也像张承志那样去正面评价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,甚至有一种“青春无悔”的情感色彩,那么道歉与否在他们那里也就不可能存在了。
其次,当真相大白之后,他们或许会觉得委屈,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,也大都付出了沉重代价。这个代价不仅是荒废了学业,而且因为后来的“上山下乡”而受到变相的惩罚。法国学者潘鸣啸在《失落的一代: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(1968-1980)》(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)一书中指出:“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下放青年下乡,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。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。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,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,有的是即时反应,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。”如果当年批过斗、打过人的红卫兵意识到他们已被变相惩处,自己的负罪感或许就会减弱许多。
如果排除以上两种情况,打过人而不道歉的心理就会变得更加微妙复杂。打人者若干年后但凡有了“良心发现”,便会意识到当年的“革命行动”既让自己蒙羞,也让自己负罪。道歉本来是减轻道德重负的一种方式,但道歉本身又使自己置身于光天化日之下,他们将因此从“匿名”的幽暗中走出,经受众目睽睽的拷问。或许正是这种颇为矛盾的心理,使他们选择了沉默。
当然,我们也应看到,已经有人打破了这种沉默。2010年6月,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学生写道歉信,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程璧老师“请罪”,一时成为话题。44年后,年过花甲的学生向86岁的老师道歉,舆论普遍认为是“带了个好头”。道歉者因此获得了某种心灵自由,程璧老师回信中那句“你们也是受害者”,也让许多人感动。然而,在这种皆大欢喜的背后,我依然看到了隐藏得更深的问题。细读那两封道歉信,申小珂当年虽是看管“黑帮”的“典狱长”,“但我没有打过您,没有折磨过您”,而只是言语“教训”。而另一位学生胡滨则引申小珂另一封来信,说出了他率先道歉的原委:“‘只有犯错不大的人,才好写这信——压力轻些。’(指他当过‘典狱长’,但没有动手打过人)‘这种信只有我这样的人写最合适。’(解释了为什么他首先出面道歉)他说明为什么他比动手打了人的红卫兵容易忏悔,同时也不因为后者未曾道歉而自己也不做。”
如此看来,这两封道歉信之所以能写出,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动过粗、打过人。而打过人者,或打人致残致死者(据《北京日报》1980年12月20日报道,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,红卫兵在北京一地即打死1772人),虽然也经受着心灵的煎熬(申小珂在信中说:“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,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,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。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,十分后悔”),但若是真的站出来道歉,或许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。而现在看来,有这种勇气的人少得可怜甚至几近于无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?其中很可能涉及人性、道德乃至文化层面更幽深的部分,而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,似乎更不容易。
当然,我也想告诉这位同学,“红卫兵打人”是个全称判断,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大事件背后个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。比如,贺延光当过红卫兵,却没打过人。虽然这种“没打过”不是因为道德自律,而是因为那种特殊的“家教”,但无论如何,他没有滑入负罪的深渊。如果当年的红卫兵都有这种家庭教育,且这种教育能起一些作用,红卫兵的“革命行动”也不至于走火入魔到那种程度。但问题是,当国将不国时,家风、家教、家规等的作用也微乎其微乃至荡然无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之所以变成“大革文化命”,显然就是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人伦秩序开始的。而贺延光能在那个时代心存敬畏,大概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吧。
(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所所长、教授、博导)
加拿大华人网 http://www.sinonet.org/ 
